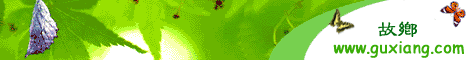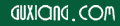|
 |
|
小麻雀之死的联想
|
|
秦洪志
一只小麻雀死了,没有伤痕,弄不清它的死因,只是它静静地躺在顶楼那热得发烫的隔热板上……
谁曾想到,麻雀的命运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迁竟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,当我看见小麻雀之死,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压得我仿佛喘不过气来,谁也不知道,谁也不能保证,它是否就是最后的一只死得不明不白的小麻雀,人与鸟儿们和谐相处,人与动物们和谐相处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能否成为我们未来的时尚,今天的呼吁也许就更是一种责任。
曾几何时,这里是麻雀们的天下。清晨,灰暗的天空刚刚现出一片朝霞,一丝丝亮色透过窗前,麻雀们就在我们的窗前、在院坝前的核桃树枝上、在瓦屋的屋檐上、在屋后的竹林里在后山的树林里、到处都听见他们欢快的叽叽喳喳的叫声,我记得童年的许许多多的梦,是伴随着麻雀们欢快的叫声,或者在天空中飞翔,或者在树林中跳跃,或者在草丛的嘻闹中度过的。麻雀们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妙的回忆,当布满朝霞的天空,风和日丽的美景,淀蓝的天空下,一大群一大片的麻雀们从头顶上飞过,落在电线杆上、杏树上、竹林上、屋檐上,那一份喧哗与宁静,一一浮现在我的脑海,我深深地知道,这一切都变得遥远起来。
无论是成年人或是年青人,是亲眼所见或者是听长辈们介绍,麻雀们经历的苦难我们历历在目:1958年,在全国一片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声中,人们为了大炼钢铁,把家里所有的农具由熟铁炼成了生铁;全民大炼钢铁已砍伐了大量的树林,麻雀们借以栖身的木头平房也拆去不少,让鸟儿们已无立足之地,麻雀又被列为“四害”而遭到全国上下一致围剿,人们把麻雀列为“四害”的理由是糟蹋粮食。更令人吃惊的是,当时全国上报的粮食产量已超过天文数字,“亩产万斤”已十分普遍,“亩产十万斤”也不稀奇,据说粮食吃不完的问题已列入重大议题,专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加速粮食转化,以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。可是,伟人们一挥手,向麻雀口中夺粮的战斗打响,麻雀履灭的厄运从此降临。人们为了除“四害”,消灭麻雀的历史场面是如此壮观:全民“邀”麻雀,五步一岗,十步一哨,房顶上、山坡上,人们抢占一切制高点,占领一切有利地形,万众一心对麻雀穷追猛打,不让它有一丝喘息机会,打死的、累死的不计其数,人们再也难见麻雀的踪影。
对麻雀们来说,五十年代的恶梦渐渐过去,人们用平静的眼光来评价麻雀的是非功过,吃粮吃虫毁誉参半,争论中漏网的麻雀数量有了恢复性增长,专家开始为麻雀恢复名誉,从“四害”的黑名单中除了名,渐渐地又可以闻听到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。可是,小小麻雀的生存力量实在是很有限,人类主宰着它们的命运。毁林开荒,环境恶化,农药大规模使用,气候变暖,垃圾成堆,到处都是环境污染,麻雀们再次面对种族生存的严峻考验: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地方搭窝,石头缝、瓦屋沟、草树堆都是搭窝筑巢的好地方,可是这些地方越来越少;吃的东西么,虫子有农药、植物草籽有农药、喝口水也有农药,天敌倒是越来越少,但也得防着冒出个“二百五”朝着自己背后放冷枪;就这么个生存环境,麻雀家族还能兴旺么?鸟类家族还能兴旺么?麻雀们早晨忧心冲冲地飞出去,不知晚上还能归来否?……
小麻雀静静地躺在顶楼那热得发烫的隔热板上死了,没有老麻雀们的叽叽喳喳的哀号,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,出奇地平静,一只小小的麻雀死了,而我们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,不知我们应该熟视无睹,还是应该警醒?
加强环境保护,减少环境污染,维护生态环境,努力营造自然生态达到一种和谐,人与鸟儿们和谐相处,人与动物们和谐相处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成为我们今天的追求,未来的时尚。我希望,这也许就是最后的一只死得不明不白的小麻雀,被静静地安葬在一个小小的土堆里。它的死,唤起人们的一种警醒,努力去承担起自己对保护环境应尽的责任。为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和质量,去找回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的故事,去追寻“门可罗雀”人与鸟儿们和谐相处的场景。
为一只小小的麻雀之死写一篇文章,以唤起人们对环境的关注,我的呼吁也许就不算是小题大作,更是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。我们生活在喧啸的城市里,渴望着“鸟语花香”的世界,即使我们培植了花园,有了“花香”,缺少了“鸟语”也就少了一份美丽。环境的现状不能不令我们担忧,森林植被的减少,无论是培植的公园,还是农村的山林,到处都难以听见鸟儿的声音。我们走过江西的庐山,在那“天生一个仙人洞,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奇妙世界里,有了山、有了险、有了奇石美景、有了苍松翠柏,给我留下最深的遗憾就是没有听见一声鸟儿的歌唱,缺少了大自然的“鸟语”,我们又岂能欢歌笑语,留下的那份冷清给了我们更多的忧虑,这才是我最沉重的记忆。“鸟语花香”组成了大自然的和谐和美丽,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,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,珍惜生命,爱护环境,保护鸟儿,从我做起。愿所有的老麻雀、小麻雀,在自由的天空中飞翔,在林子里嬉戏,生活才是美好的!
|
|
 |
|
 |